牧者之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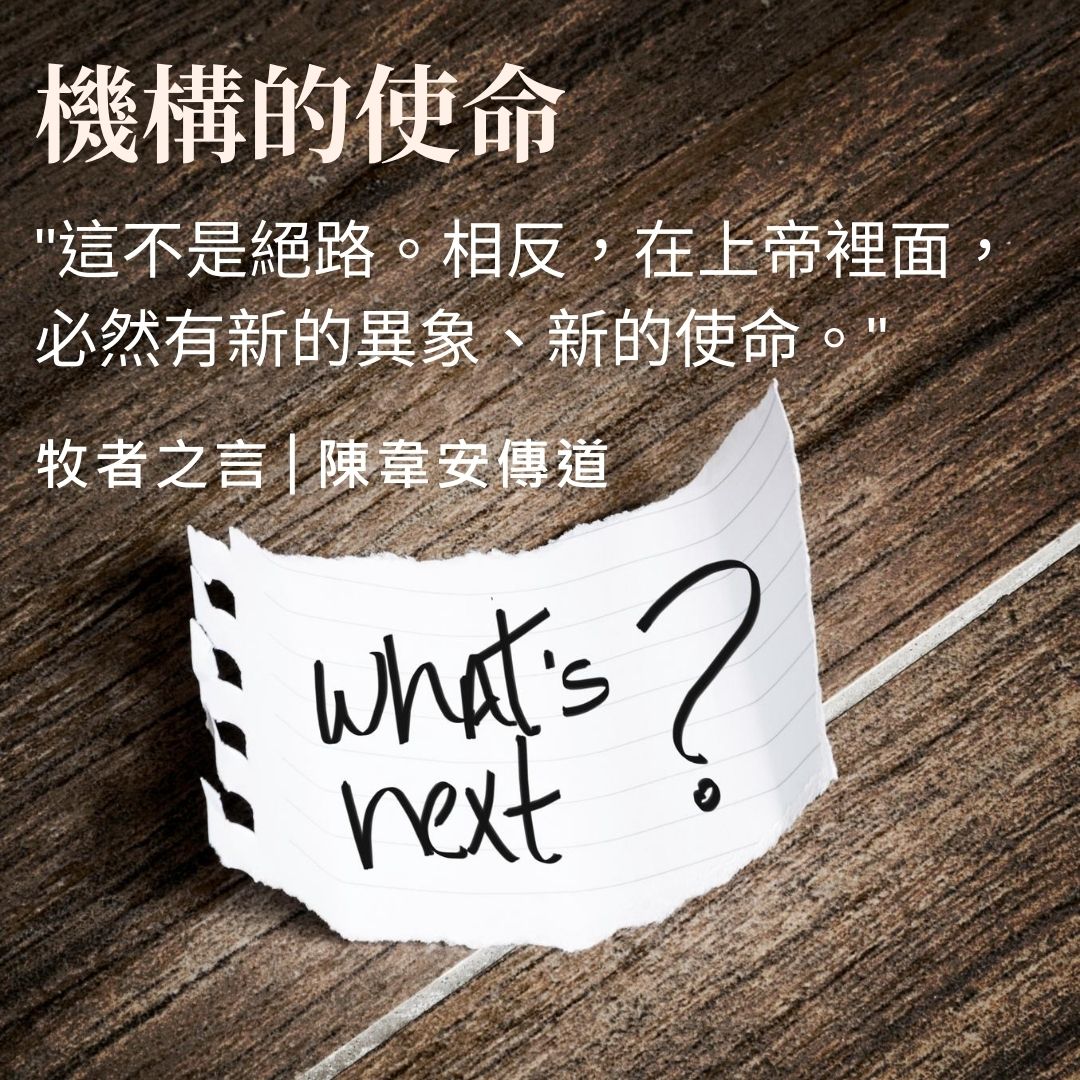
近日聽聞不少基督教機構面臨倒閉,感觸良多。
面對疫情,全球經濟衰退,教會雖不算是最嚴重的行業,但不少基督教機構成為第一批面臨結業的受害者。為何是基督教機構?從整個教會生態結構的角度來看,基督教機構處於財政生態的下游——機構的資源大部分來自堂會捐獻或個別大金額奉獻。因此,面對經濟不景氣,機構是首當其衝的犧牲者。
有人說,面對倒閉潮,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,讓基督教機構重新思考自己的使命與異象。不過,怎樣思考呢?這正是本文探討的重點。
先談談「基督教機構」之美。基督教機構的出現,源自一個廣義的教會觀。作為廣義教會的一部分,基督教機構填補了普通堂會不能發揮的功能,專門服侍一些「獨特」的教會使命。譬如說,神學教育、差派宣教士、文字出版等等。
因此,基督教機構的存在,從來都必然源自一個「獨特」的使命與異象——請留意,「獨特」二字乃是重點。所謂「獨特」,就是說它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。它是具體的、處境性的、會過時的。任何異象都必需要是會過時的。正如我們說:「不能被驗證的命題,就不是命題。」同樣地,永不過時的異象,就不是異象。
試想想,一個永不過時、超級無敵、永不落空的異象:「廣傳福音,造就門徒,靈命進深,愛主更多」之類的,它們不是異象,而是廣義教會的存在目的。它們很對、很好,但不是機構的異象。既然基督教機構是廣義教會的「部分」,它的使命也必然需要是「部分」。引用神學的術語,它必需是「事件」(event)。基督教機構的重點是「發生」。它的存在,就是為了讓事件發生。因此,它的使命與異象必然帶着時間的概念。它誕生於某個時代,也大概必然結束於某個時代。
因此,任何機構的領袖都必需要是一位現實的理想主義者。或,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。
機構是一個教會事件,但它無疑也是有生命的組織——求生、保命、生存,對機構來說,天經地義、人之常情!任何堂會或機構領袖,他/她都必需擁有「使命」與「保命」的思維。尤其是機構領袖,他不可忘記機構的使命,卻每天面對着保命的問題——籌款、競爭、宣傳、數字等等;只有使命卻不懂保命,機構就沒有「命」來實踐使命;不過,更大的試探是:機構一心只是想着自己的命,卻忘記了起初的使命。因此,機構同工面對最大的難題是:如何帶着「使命」去「保命」?
我們這一代的基督徒領袖,大概都是守業的一代——這話沒有貶義。我們都習慣、被要求去保命。上一代人把心血交付了我們,我們豈敢不慎重保存?不過,正如我一開始所言:機構的使命,必然會過時。假若機構的「使命」過時了,「保命」也變得沒有意義了。
不。這不是絕路。相反,在上帝裡面,必然有新的異象、新的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