牧者之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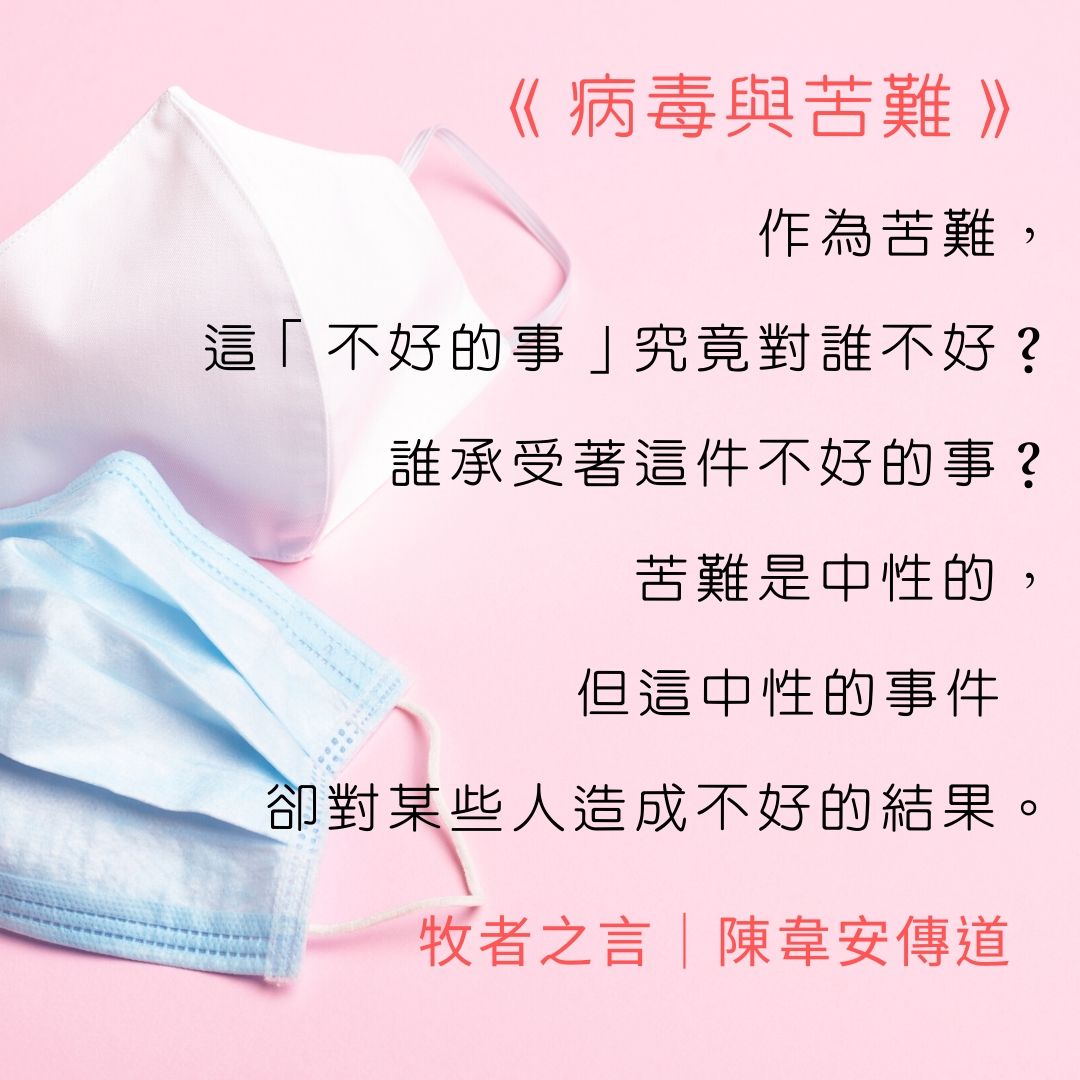
病毒是一個苦難的問題。
甚麼是苦難?苦難是不好的事——我相信這是一個比較穩健、廣義的定義吧。無論是癌症、風災、被搶劫、親人被害、銀行倒閉、家散人亡,無論它們的過程如何、原因如何、科學原理如何,它們的相同之處大概都是一樣:不好的結果。
不過,苦難本質上是中立的。地震是地殼的移動、颱風是熱帶氣旋的臨近、癌症是細胞不正常的增生、瘟疫是病毒的傳播。從道德的角度來看,苦難沒有犯罪的意志。譬如說,病毒只是沒有意識地佔有人體細胞組織,從而破壞人的生命。病毒不是討厭你,也沒有懷着惡意傷害你。它只是客觀地傷害了你;地震也是如此。所謂「地震」,大概只是人類剛巧把建築物興建在會震動的地殼之上而已。當然,說這種話實在非常涼薄。
隨着人類科學的進步,人類逐漸能夠掌握宇宙大自然的定律與原理。人類知道「瘟疫」並非無緣無故的,也不是「從天降下」。人類掌握了「苦難」事件的細節,並發現這些細節科學上的中立性:瘟疫就是空氣傳播着非常微少的東西,我們稱之為「病毒」。不過,對人類來說,病毒的「毒」字似乎就帶有一種負面的意義。
因此,苦難作為一件「不好」的事,它本來帶着主體性與價值觀的問題。作為苦難,這「不好的事」究竟對誰不好?誰承受着這件不好的事?苦難是中性的,但這中性的事件卻對某些人造成不好的結果。病毒是不好的嗎?對人類而言,當然是。不過,網上也有傳因着疫情的緣故,數百萬隻瀕臨絕種的海龜能夠在無人的海灘上生蛋。
我想,這正是苦難問題的核心——苦難的重點不在於它的客觀性,而是在於它的主觀性。
我們問:既然人類已掌握科學的細節,難道苦難的問題就能夠被終極解決了嗎?我們知道病毒如何形成、人類如何受感染、地殼如何移動、颱風如何產生,我們就能解答苦難的問題嗎?似乎不。或許科學能夠掌握苦難事件的客觀性,但它卻未能回答人類主觀性問題:「為甚麼?為甚麼是我?(Why? Why me?)」
正如小學生們都掌握的蹺妙:一個「為甚麼」的背後,永遠有另一個邏輯上的「為甚麼」:
「為甚麼會我會有病?」「因為病毒侵入了你體內的細胞。」
「為甚麼病毒侵入了我體內的細胞?」「因為某年某月某日病毒進入你的身體。」
「為甚麼某年某月某日病毒進入我的身體?」「因為......」
沒完沒了的。最後,我們只能歸咎於那「第一因」:上帝。
還記得約伯記的尾聲,耶和華在約伯記四十章與四十一章一連串的生物學問題:
「在牠防備的時候,誰能捉拿牠?誰能牢籠牠穿牠的鼻子呢?
你能用魚鉤釣上鱷魚嗎?能用繩子壓下牠的舌頭嗎?
你能用繩索穿牠的鼻子嗎?能用鉤穿牠的腮骨嗎?
牠豈向你連連懇求,說柔和的話嗎?」
或許,人類科學終有一天能夠完完全全解答以上科學問題。但是,真正難以解答的不是這堆科學問題——它們都只是中立的過程與現象。真正難以解答的,其實是「約伯-上帝」的主觀性問題。因此,基督教信仰所提供的,並非苦難事件的客觀性,而是叫受苦者在主觀的苦難中,思考自身與上帝存在的主觀答案:
「我從前風聞有你,現在親眼看見你。」(伯42:5)